BookBar側記│七月場《問題不在性別,而在權力——#MeToo運動的意義與局限》
「2025年帶一本書來Book Bar」 7月場
《問題不在性別,而在權力——#MeToo運動的意義與局限》活動側記
「帶一本書來Book Bar」七月場,邀請到伴盟創會理事長許秀雯律師,分享Martha Nussbaum的《傲慢的堡壘:重探性侵害的問題根源、問責制的未竟之業,以及追求性別正義的道路該如何前進?》。主持人由暖暖Sunshine協會成員、兒少性侵追訴權釋憲案訴訟代理人蔡尚謙律師擔任,他在開場拋出讓人深省的扣問:「有沒有更好的方式來對待這些傷痛?」
▶️#MeToo的羞恥轉向
從好萊塢#MeToo到臺灣#MeToo,秀雯律師認為這個運動可貴之處,是讓倖存者發聲、打破沉默,讓羞恥轉向。她談到法國近期吉賽兒·佩利寇(Gisèle
Pelicot)性侵案件的司法審判,有別於過往的案件,72歲的吉賽兒選擇公開審理、放棄匿名權,要求法庭播放證據、公開案件細節,勇敢控訴其前夫與其他50名被告,在她被前夫下藥昏迷期間對她性侵,讓羞恥從受害者轉向加害者。值得一提的是,她選擇保留夫姓(加害人Dominique Pelicot的姓氏),是為了希望這個姓氏對家族的子孫而言,能夠不是一個羞恥的印記,而是象徵勇氣的姓氏。
作為對照,秀雯律師回顧自己生命歷程中具體接觸性侵課題,是1994年師大國文系教授性侵女學生的案件。當時,女學生在學校圍牆上噴漆指控該名教授,事情才被揭露,卻也招致強烈的反撲。當時尚未有性別平等工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或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校方在處理過程也有非常多的瑕疵,另外校內校外也有些人質疑這是不是師生戀、情感糾紛或錢財勒索,責難女學生為何當下不求救、為何第一次發生後會有第二次……反映出人們對於「熟識者性侵」以及「利用權勢性侵」普遍的不理解,以及性暴力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責備受害人」迷思。
由於當年的「強姦罪」(現在的強制性交罪)為告訴乃論,僅有6個月的追訴期,女學生無法再提出告訴。後來,反而是教授的太太以通姦罪來控告女學生。整件事變成由於女學生知道對方是已婚身份,並承認有發生性行為,而被認定構成通姦。依據刑事訴訟法,通姦罪的提告一開始必須同時提告配偶與所謂的第三者,但是在過程中允許單獨撤回對配偶的告訴,讓男教授從加害位置轉為證人身份,並將整起事件界定為一個合意的通姦。女學生最終被判通姦罪成立,還得民事賠償數十萬元,最後由當時婦女團體及許多女教授協助募款繳納那筆賠償。
秀雯律師感嘆,陪伴師大案女學生的過程,是她第一次與性侵法制和父權社會的肉搏戰,這個經驗對婦女運動是重大挫敗,自己也覺得非常崩潰與震撼。當時還是法學院學生的她,親眼目睹法律未必帶來正義,也曾懷疑自己是否能繼續走法律這條路。秀雯律師進一步指出,女學生會重複受暴,是因為很深的羞恥感,使她長期沉默,進而加深受傷程度。然而,很多人依然無法諒解受害者的沉默,難以同理揭露的困難。因此,#MeToo運動的意義不僅打破沉默,也在於要藉由集體發聲和公眾課責讓羞恥轉向。
▶️公開控訴的可問責性
接著,秀雯律師指出#MeToo另一特徵,是不仰賴正式法律體系來定罪,這有其優劣。按作者Nussbaum的觀點,公共羞辱不應取代正當的法律程序。當然,相較於過去許多控訴會被掩蓋、吹哨者可能面臨報復等情況,#MeToo迫使社會認真去直面這些控訴,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然而,也必須看見這個運動的局限與潛在危險,就是當「可問責性」缺乏嚴謹的程序與檢證時,確實也有可能會傷及無辜或不符比例原則。人與人的關係是複雜的,若僅仰賴這一股揭弊的輿論力量,難以真正處理長期系統性存在性騷與性暴力的犯罪。秀雯律師坦白,法律終究不完美,無法解決所有問題,創傷往往也未必能藉由法律程序而得到撫平和復原。
▶️性別的傲慢與物化
作者Nussbaum在比較晚年時期才書寫《傲慢的堡壘》這本書,她本身也是性侵倖存者。這位令人敬仰的美國女性主義哲學家,學術成就卓越,在多年前曾投書一段經歷,揭露自己跟某位男明星的約會,從合意開始,卻最終在對方粗暴違反她意願的方式下發生性行為,對她而言,那其實是性侵的過程。
秀雯律師指出,這本書提出一個關鍵問題: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為什麼人會傷害人?這個「為什麼」是很多倖存者的痛苦。顯然,這沒有簡單的答案。書中提出一個系統性的解釋,借用《神曲》三部曲中但丁進入煉獄的情節——在煉獄中,看見對摺的人,眼睛只看見自己、看不到別人,這個罪行就是傲慢。傲慢的特性,是自視甚高、自我陶醉感較高、認為自己比他人優秀、自戀,同時缺乏同理、不在乎別人的感受,不把別人當作平等的主體。當傲慢者與別人互動時,無法傾聽、也不去理解對方想要表達的意思。
關於性別的傲慢,Nussbaum在書中(中文版頁67)引用彌爾的話:
「想像一下這對男孩來說代表了什麼,在他長大成男人的過程中,他會相信即使沒有任何長處或是自己的努力,或者雖然他可能是最輕浮、最空洞的人,最不學無術也最麻木的人,但是只要他生而為男性,按理說他就優於人類種族的另一半中每一個人:或許其中有些人當真每天、或每小時都感覺到自己具有優越性,(這些男性)只是出自傲慢,而且是最糟的那種傲慢,他們的價值只是來自於剛好取得的優勢,而不是自己的成就。主要就是覺得自己位於另一性別的全體之上,而且掌握對該性別的任何一個人的人格權威。」
書中也提到英國殖民者刻意維持印度男性對女性的權威,對殖民者來說這個縱容性別不正義的策略有助於鞏固殖民者的統治與權力:讓印度男性有他可以完全支配的領域,這樣他就比較不會想要反抗「英屬印度」。
「傲慢」和「物化」是本書提出來的兩個關鍵概念,所謂物化,就是將人視為「客體」看待,包括工具化、否認自主權、無生命、可取代性、可侵犯性、可擁有性、否認主體性、使消音等等。
在吉賽兒案件中,部分被告辯稱已經取得先生同意,或認為是夫妻協議好的,對此,秀雯律師質疑,這些被告為什麼竟然沒有一刻想要確認太太本人的意願?若非將女性視為先生的財產、或徹底藐視女性主體性和自主性,又怎能將那個過程簡單當作一個色情劇本而參與其中?
事實上,這些被告跨越年齡和族裔,並沒有太多共同性,而也有許多研究指出性侵加害者其實就是一般人。是什麼文化會讓一般人成為性侵加害者?Nussbaum的答案,是傲慢與物化。當你不視他人具備自主性與主體性時,對方說的yes or not,以及會有什麼感受,是否會受傷,對你而言都不重要。
▶️體制與文化的改變
秀雯律師進一步談到,這也涉及法律體系如何處理性侵問題。過去,臺灣法律不把婚內強暴當作強暴,認為進入婚姻關係後就默示讓渡對性與身體的同意權,形同某特定身份的人對另一人的身體可予取予求;如今,一般的強制性交是非告訴乃論之罪,而婚內的強制性交也被認定是犯罪(不過是告訴乃論之罪)。她也提到,早期強姦罪是落在刑法的妨害風化章,強調這個行為是妨害社會的善良風俗;現在,已改為是妨害性自主罪章,反映觀念的重要轉向。
談到鄧如雯案,秀雯律師指出,過去法律界定的正當防衛並沒有涵蓋受暴婦女的經驗,後來才有家庭暴力防治法。臺灣相關性平的立法,其實都經歷傷痛的悲劇後才推動而成,包括彭婉如之後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葉永鋕之後的性別平等教育法。她強調,如果都要藉由重大悲劇才能帶動法律體制與文化的改變,代價真的太大,希望我們的社會能夠對於性別人權議題多一些關注與思辨改革的空間。
針對當代性知識的來源,秀雯律師認為許多人對性的理解來自色情片、同儕吹噓,或真假參半的資訊,往往充滿誤解與偏差。她不反對色情,認為好的色情應該是愉悅、合意的;而戀愛與親密關係的發展,是需要練習,要將對方視為性的主體存在、尊重其自主權。她進一步補充,若性腳本與文化不改變,單靠「課責」(法律或公眾的課責)也無法真正解決問題,因此,還是得從根本去思考如何可以不成為「行為人」;而作為旁觀者,每個人也都有介入的責任,如果加害人就是一般人,表示「強暴文化」很可悲地構成我們文化中的一部分,意思是我們的體制和文化,作為一套完整的「權力的食物鏈」,性別不平等僅是其中一環,本身就是性侵問題的根源,也因此必須做出改變。
最後,尚謙律師也提出,司法實務中也常出現「完美被害人」的迷思,甚至檢討受害者。他分享作為優勢性別位置的一方,如何學習克制而避免傷害他人。他也坦言,即使是吹哨者,也會焦慮自己的控訴是否「罪責相當」;但真正該問的是,為何社會給予這些創傷經驗者那麼多的包袱與壓力。他強調,揭發不是為了報復與羞辱,而是為了正視傷害、追求修復性的正義。
發佈日期: 2025/08/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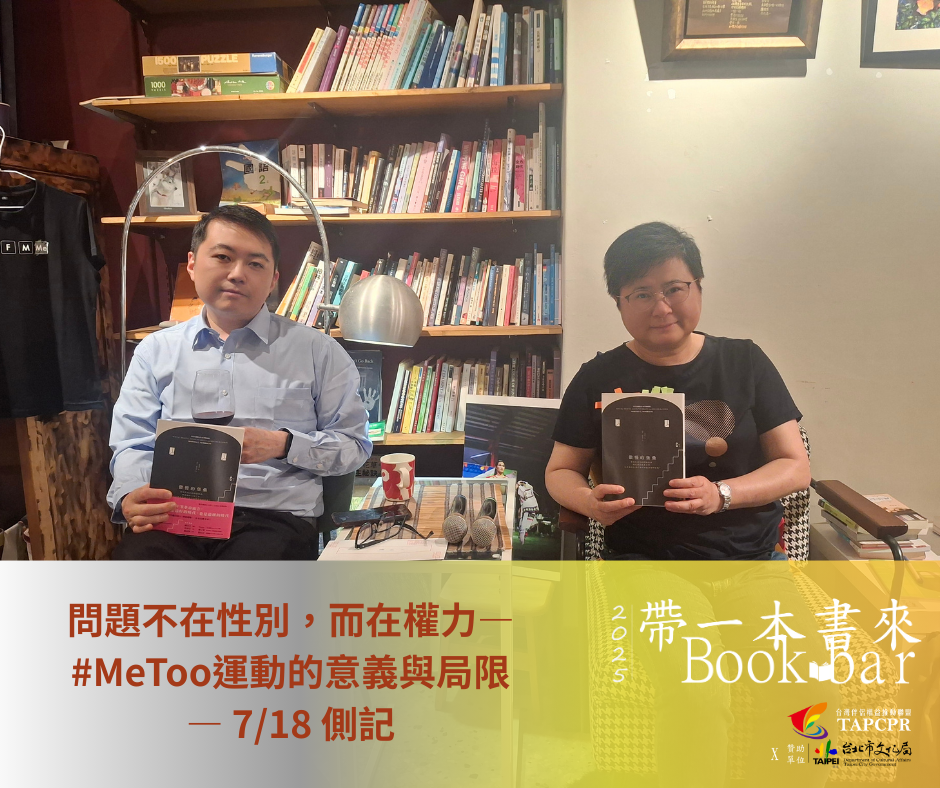

轉
推
+1
寄